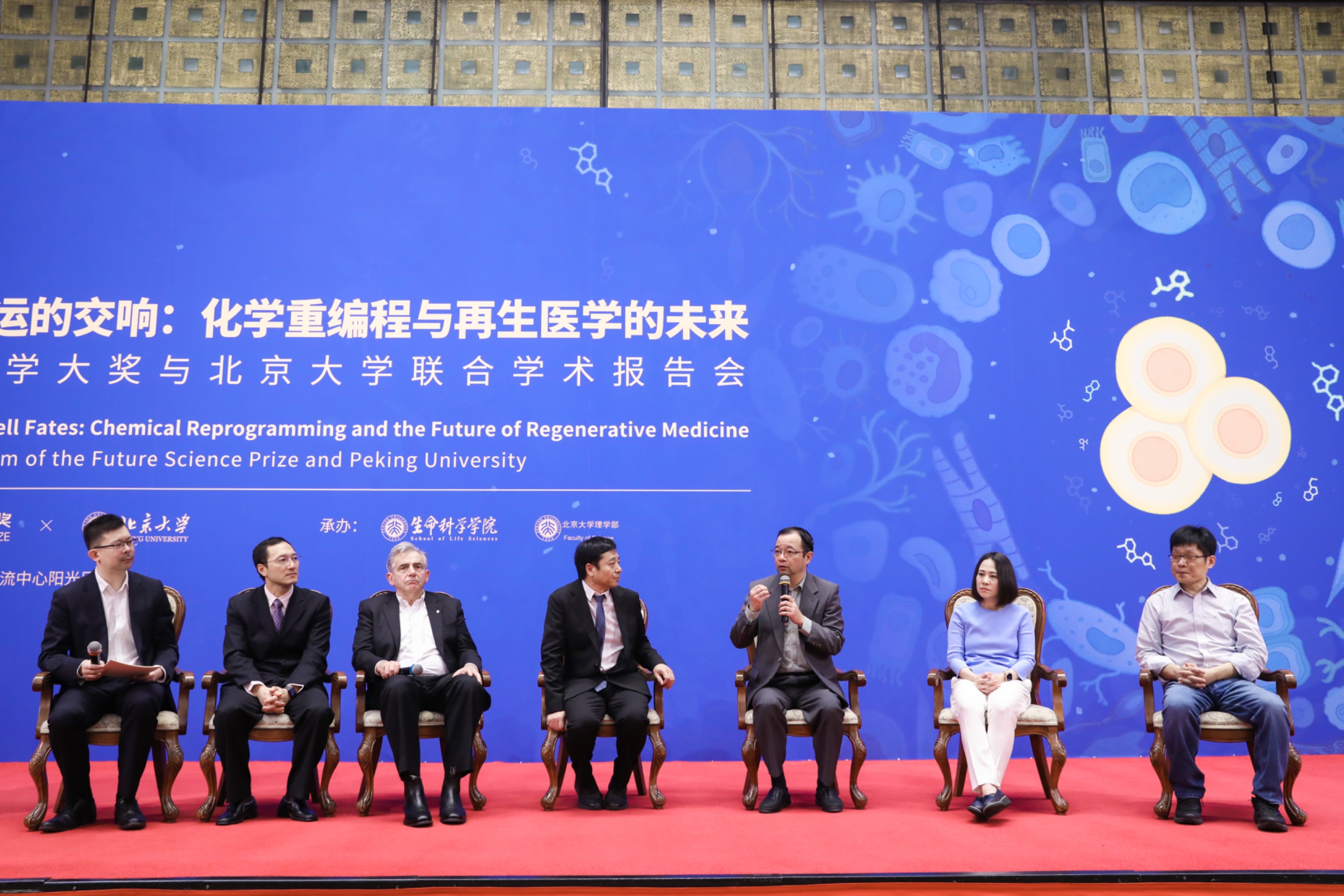骆利群的人生,可以用从“神童”到“名家”来概括。
15岁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30岁成为斯坦福大学博导,之后又陆续当选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员、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和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
他在神经科学领域的工作,为理解人类脑功能和治疗脑疾病打下了重要基础。
近日,骆利群作为2021未来科学大奖周Program Committee联席主席在大奖周期间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分享了疫情之下高校师生的科研新常态:去不了实验室的研究生、拿到奖学金却拿不到出国签证的博士后、遭遇就业寒冬的毕业生……他们是如何应对的?
此外,他还分享了发现科学好问题的“3步法”,帮助大家找到科研的最佳着力点。
看看,是不是你需要的。

骆利群
斯坦福大学文理学院讲席教授,生物系教授,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神经生物系名誉教授,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员,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86年获得中国科技大学学士学位,1992年获得美国布兰迪斯大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从事博士后研究。1996年被斯坦福大学生物系聘为教授。研究领域为神经科学,重点是大脑神经网络的结构和构建。
《中国科学报》: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多变化。一些留学生或期望出国留学的研究生都会面临更大的挑战。请您从自己的切身经历出发,讲讲现在应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骆利群:
的确如此。新冠疫情产生了很多副作用,科研人员的境遇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感觉受到最大影响的群体还是研究生和博士后,他们在科学领域还处于成长期,做实验出成果只是一部分,还需要跟其他科学家面对面的交流,学到很多新的东西。但是受疫情影响,很多线下会议都取消了,这对他们来说的确是很大的一个损失。
就业也是一个问题。我有两名非常优秀的博士后,因为遇到了疫情,去年在求职中花费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当然他们现在都找到了很好的工作,但我总是觉得如果没有疫情,他们还能找到更好的工作。
此外,还有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去年,我们实验室本来应该迎来一位非常优秀的中国博士后,他已经申请到了斯坦福的荣誉奖学金,但因为疫情,签证迟迟签不下来。就这样,我们实验室失去了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博士后,而他失去了来斯坦福深造的机会。
所以,毫无疑问,新冠给很多科学家、研究生和博士后都带来了很大的难题。
《中国科学报》:您刚才提到这位博士后的情况,在当下也是比较典型的。对这部分人群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骆利群:
对个人成长来说,有些损失还是很难完全弥补。
像这位博士后,即使他不来斯坦福,我也可以远程指导他去做哪些工作,但问题在于,我们可能失去了一些偶然讨论中迸发的灵感,可能就会少发现一些创新的机遇。
但我知道现在中国的科学研究水平已经发展得很好了,我的一些中国学生在毕业后也优先选择了回国工作。所以我相信这些优秀的年轻人,即便不来斯坦福也能遇到很好的机会。
所以就是在现有的环境里,尽可能最大化利用一切能利用的资源,be original,be creative。
《中国科学报》:我们也看到,不管多么艰难的环境,各国科研人员依然在努力地继续前行。能不能讲讲您和您身边的科研人员是如何应对这些新出现的挑战呢?
骆利群:
大家都在适应中。
很有趣的是,疫情似乎对我们发论文没有影响,反而好像有一点促进作用。
我们实验室近期有3篇论文,都是因为学校实验室关闭,实验被迫中断,大家来不了实验室,在家没事干,说:ok,那我们就写文章吧。总结一下之前实验已经取得的结果,看看能够写一篇什么文章。
结果他们发现,得到的结果已经足够写文章了,而且写得很好。最后发表在很好的期刊上。
当实验被迫中断的时候,大家其实有了更多时间去思考问题。
我们也在用一些线上会议软件,这种软件开大会效果不好,但开小会还不错。
我去年开了两门课,疫情期间都转到线上,大课的效果就非常不好,但一门12个人的小课,主要是一起读文献并讨论的,就让我感到比课堂上的效果好多了。大家可以把文献放在屏幕上,可以划可以点,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非常好用。
《中国科学报》:从这样的经历中,大家是否也学到了一些东西?
骆利群:
是的。尽管后来实验室开放了,但中间大约一年的时间,每天只能来做半天实验。怎么办呢?在实验室的半天要提高效率,在家的那半天可以好好读文献、想问题、分析数据。
长远来看,这种锻炼是有好处的。
《中国科学报》:疫情给科研人员带来了空间上的“隔离”,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科学共同体的交流合作,对此你们怎么应对呢?
骆利群:
我觉得疫情对已经开展的合作影响不大,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影响了潜在的合作机会。
很多合作,是科学家面对面谈,特别是一些非正式谈话中聊出来的。这个现在就比较难。从今年8月开始,我又恢复了一些面谈会议。
《中国科学报》:感谢您关于疫情期间科研工作的分享。接下来请您跟年轻的科研人员分享一下,怎么面对越来越激烈的科研竞争?怎么跳出低质竞争的圈子,把科学的蛋糕做大?
骆利群:
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于要做创新的工作,要做别人想不到的工作。你如果整天跟着别人去做,100个人都做一个事情,你就得跟另外99个人竞争;但如果你做的是开创性的东西,你看到的就不是竞争的压力了。
《中国科学报》:那对大多数科研人员来说,该怎么去寻找既有创新又有价值的科学问题呢?
骆利群:
首先你要了解领域。
其次你要知道在一切未知的部分里,哪些问题最有可能在近期获得解答。比如说100个“unknown”中,有10个你或许能在未来5到10年中找到答案。
然后你就要思考,这10个“unknown”中,有哪一个问题被解决后,不仅对这个问题本身有意义,并且可以拓宽我们对更多科学问题的认识。
这3步是一个通常的步骤。
这里面有个权衡:容易解决的问题通常影响小一点,难解决的问题可能影响大一点。所以你就需要找那个“sweet spot(甜区,球拍或球棒的最佳击球点)”,在可解决性和影响力中取最大公约数。这就需要你的洞察力。
《中国科学报》:如果请您对年轻的科研人员说几句话,您会说什么?您期待他们成为怎样的“未来科学家”?
骆利群:
在刚刚走上科研道路这个阶段,年轻人会遇到很多琐碎的事情,但我建议你们把主要的精力用来思考什么样的科学问题值得被解决,然后全力以赴。你这样做了,得到成果了,后续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
所以,“focus on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