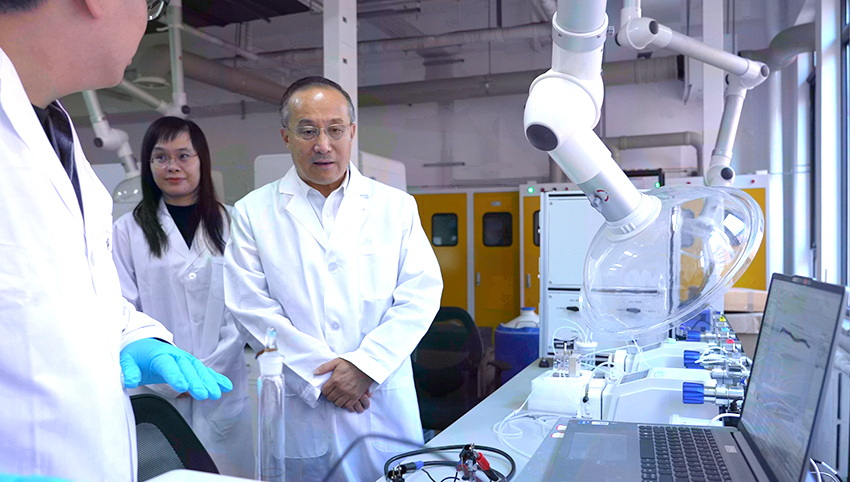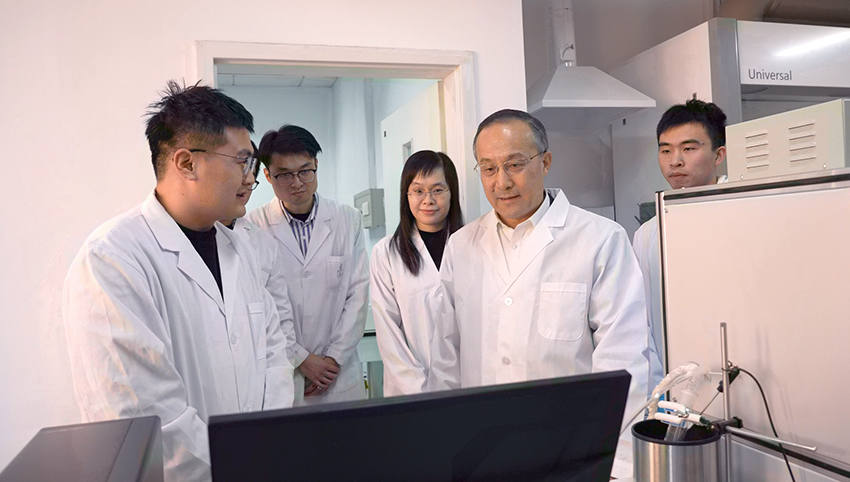文章来源于文汇报,作者姜澎、储舒婷

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研究所所长、中科院院士张杰。文汇报记者 袁婧摄
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必要前提。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如何开展有组织的科学研究,坚持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两条腿走路”,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
“由于历史的原因,过去40多年,我国基础研究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回答别人提出的科学问题,原创性仍有不足。今天,我国的科研投入总量已达世界第二,我们不能再一直做别人‘出题’的基础研究。除了选题自由的探索之外,应该更有意识地聚焦世界科技最前沿,发挥大科学研究范式的优势,在根本性科学规律的认识上取得重要突破,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要贡献。”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研究所所长、中科院院士、2021未来科学大奖-物质科学奖获奖者张杰日前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
张杰指出,大科学时代颠覆性科技创新成就往往依赖于跨学科、跨领域、跨组织的创新团队和高效的资源配置。发挥大科学研究范式的优势,必须汇聚起一批战略科学家,进行顶层设计,凝练大科学问题;要对大科学问题进行有效分解,组织分工;在实施推进阶段,要对分解后自由探索研究结果进行“重新组装”。
把大科学装置的优势转化为大科学研究范式的优势
文汇报:可否结合您的研究经历谈谈,科研范式变革将给基础研究带来哪些影响和变化?
张杰:随着基础科学前沿研究不断向微观和宏观方向推进,人类越来越需要使用大科学装置的极限探测能力,来推动对根本性科学规律的研究与发现。据统计,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上大约有40%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成果是利用大科学装置获得的,并逐步形成了以聚焦根本性科学问题、充分发挥大科学装置的优势、有组织的科研攻关和稳定的经费支持为主要特征的大科学研究范式。
像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走过的道路一样,我国的基础研究也经历了从“跟跑”到“并跑”并逐步在部分领域可以开始“领跑”的阶段。这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也对我国基础科学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即要结合自由探索和有组织的科研,发挥大科学研究范式的优势,在根本性科学规律的认识上实现重要突破。
经过过去20多年的持续投入与建设,我国的大科学装置数量已经达到全世界第二。但是,如何系统地把大科学装置的优势转化为大科学研究范式的优势,进行有组织的科研,针对最根本的科学问题展开探索,我们仍然需要不断探索与实践。
文汇报:在过去几十年,基础研究的内涵是否发生了变化?您认为就基础研究而言,我们现在处于什么阶段?
张杰: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是对自然奥秘和根本规律的不断探索。就中国而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事业的快速发展,我国基础研究的内涵在过去几十年中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可以看到,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我们越来越关注基础研究的价值,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也大大增加。我国基础研究投入从2012年的499亿元提高到2022年的1951亿元,过去十年年均增长近15%,占全社会研发经费(R&D)比重由4.8%提升至6.3%,为我国基础研究在更多研究领域实现“领跑”,在根本性科学规律的认识上实现重要突破创造了基础条件。
我目前所在的李政道研究所,也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诞生的。李政道先生一直有一个梦想,他认为,中国应该有一个类似玻尔研究所那样的顶级基础科学研究机构,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贡献。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玻尔研究所在上世纪集聚了一批杰出科学家,在整个20世纪量子科学发展乃至整个物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奠基性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引领了第三次科技革命。
当下,世界面临第四次科技革命。中国发展至今,已经有能力在基础研究领域实现更多突破,同时也必须抓住基础科学研究快速发展的最佳窗口期。李政道研究所成立的初心和使命就是建成基础科学领域的世界顶级研究所,吸引一群世界顶尖科学家,培养我国自己的青年科学家,形成自由探索的学术氛围,并且充分发挥大科学研究范式的优势,在基础研究方面解开目前仍不可理解的那些宇宙奥秘,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要汇聚更多战略科学家,凝练大科学问题
文汇报:大科学研究范式更强调目标导向、更强调科学家之间的协同创新,而科学家的天性似乎是更崇尚自由探索。那么如何更好地平衡目标导向的、有组织的大科学研究和科学家的自由探索?
张杰:有组织的大科学研究范式与自由探索之间并不矛盾。就以我从事的物理学研究为例。
一般来说,物理学基础研究目标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探索自然奥秘,满足人类对自然世界和宇宙未知的好奇心;另一类目标是为了破解阻碍人类社会发展的难题,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虽然每一个物理学家兴趣不同、擅长领域不同,但这两类目标也是每一个物理学家从事基础研究探索的共同梦想。
就社会层面来说,要平衡好有组织的大科学研究和自由探索,关键在于,要建立科学家之间的分工与共享体系,营造让科学家自由交流的机会、氛围,激发起每一个科学家心中探求未知与实现使命的强烈愿望。同时,我们还需要汇聚更多有洞见的战略科学家。
为什么战略科学家的作用如此重要?我以自己的研究举例。我是从事激光聚变研究的,这是典型的需要大团队、大装置、大投入的研究。激光核聚变反应一旦实现,除了可以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终极能源目标之外,还将使人类对自然探索的极限能力进一步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境界。目前,人类已经走到了实现激光核聚变反应输出能量大于激光输入能量的关键时刻,但我们仍有很多基础的科学问题没有解决。
2018年,我们开始组建团队时,既没有研究经费,也没有诊断设备和理论模拟程序,更没有制靶条件,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但是,团队中有不少科学家就是怀揣着实现终极能源的梦想,可以说是“自带干粮”,加入我们的联合研究团队。
围绕着共同目标,我们将实现激光聚变过程中的基础科学问题进行分解,并且不断地推进这些问题的解决。从2018年到2020年的初创时期,我们团队的很多老师几乎没有发表过一篇相关论文,非常艰难。此后,2020年开始的8轮大型激光聚变实验不断取得突破,我们解决了一批与激光聚变过程相关的基础科学问题。去年一年,我们团队的科学家发表了60多篇研究论文,今年还会有更多重量级论文发表。可以说,联合研究团队在向重大科学目标不断推进的过程中,自由探索也不断取得进展。
在我国的基础科学研究中,大约有80%-90%是基于科学家的自由探索,当科学家们内心深处的梦想被激发,他们的自由探索同样会解决大科学研究中的众多基础科学问题。重要的是,发挥大科学研究范式的优势,有一批战略科学家共同关注选题、研究推进、问题拆解、成果“组装”等整个基础科学研究创新链的每一个环节。当然,除此以外,还要有稳定的经费投入、评价机制等科研管理体系方面的变革。
建立科学评价体系,支持开展高风险原创性研究
文汇报:原创性的研究往往是高风险的研究。在科研人员的评价方面,如何建立更好的评价机制,让科研人员能心无旁骛、坐住坐稳“冷板凳”?
张杰:确实,最具创新性的研究往往是高风险的研究。紧紧围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当前,我们还需要在整个科研评价体系开启更多的改革。
应该看到,在传统的以论文为主导的评价体系下,一些科研人员会更倾向于做发表论文更容易的“自由探索”,即只做“能发表好论文的科研”。可以说,这种现象不仅在物理学,也在其他一些学科中发生。事实上,当科研人员都倾向于从事更容易发表论文的研究,这种急功近利的风气不仅给年轻人的成长带来负面影响,也会有损学科和科研的健康发展。
不过,也可以看到,我国的科技创新激励体系正在发生可喜的变化。比如,我所在的激光聚变联合研究团队中,有两位重要成员分别来自中科院物理所和上海交通大学,是我们8轮大型联合实验的实验诊断值班长。他们对于激光聚变实验诊断有着独到的理解和高超的技术,去年,他俩因为对激光聚变研究作出的实际科研贡献、而非因为发表论文,在各自的单位都晋升为研究员。又比如,我们项目中的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已有多名科研人员凭着实际科研贡献而不是简单的论文发表,获得了职称晋升。可以说,这样的评价体系的建立,不仅对科研人员本身是一种激励,对更多年轻的科研人员和学生来说,也无疑带来正向的激励。
因此,在大科学研究中,从长远来看,科研人员在从事重要科学问题的探索中可能取得进展甚至突破却不能发表更多论文,应该把这些贡献纳入实际的科研奖励和资助体系。
文汇报:从科研管理的角度,您可否谈谈,如何更好引导青年科研人员沉下心做研究?
张杰:对于青年科学家,应该给予他们一定的时间和稳定的支持,不要过于干涉他们的自由探索。每次谈到这个问题,总有人会举一些极端的例子来佐证基础研究需要10年、15年甚至更长时间才会出成果。确实,基础研究需要耐得住寂寞,要甘坐“冷板凳”,但是在一个科研机构中,在氛围足够宽松、科研人员之间交流足够充分的情况下,六年基本也足以判断某个研究的价值。
在李政道研究所,我们已经聚集了一批世界级的科学家,还有一批充满梦想的青年科学家。每一位年轻的科研人员进来之后,都会配备1-2名资深的科学家“辅导”。在我们设置的六年聘期中,通常只在第三年对他们的研究进行一次诊断性评估,给他们的研究提一些建议,青年科学家可以选择是否接受建议,直到第六年我们会对他们的研究进展和未来发展的潜力进行最终评估。
归根到底,我们需要给年轻人更多自由探索的空间,同时也需要一个稳定的科学研究支持体系。当然,目前要推进大科学研究范式,仍然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大科学装置建设经费的申请过程过长,还缺乏稳定的运行经费渠道,一些国际学者难以申请到研究经费等。但是我相信,随着我国对基础研究改革力度的进一步增强,在不断改革的过程中,会探索出更多有益的经验、取得更多的成绩。
3月21日文汇报第四版
原文来源: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60929483482215560&wfr=spider&for=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