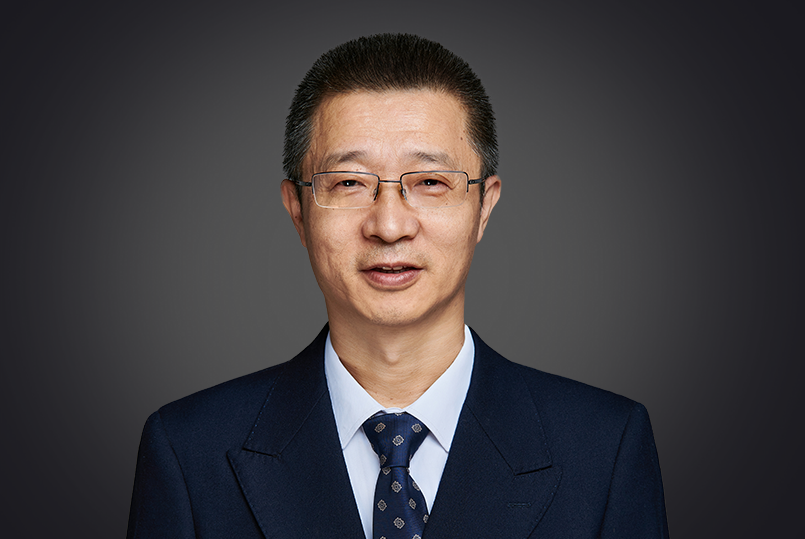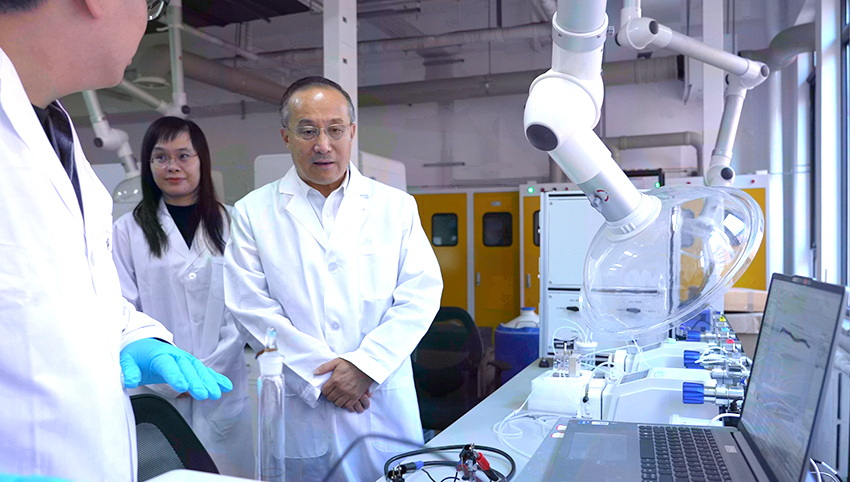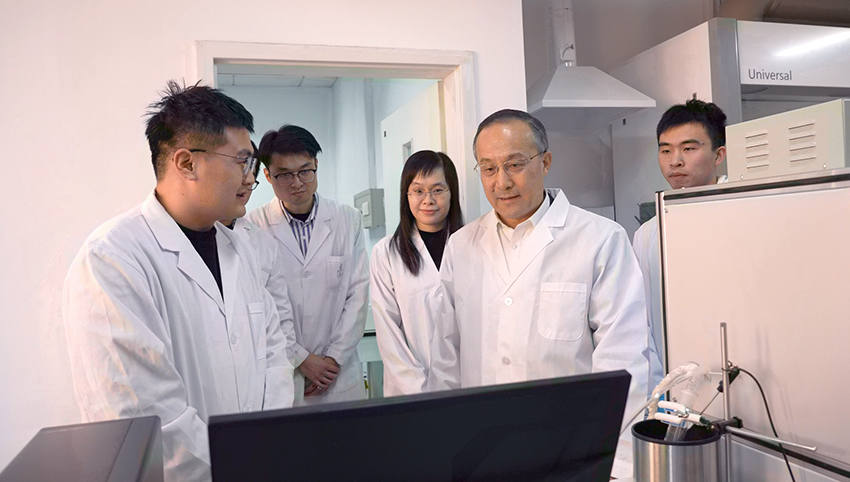“从造纸厂走出来的顶尖科学家”,提到柴继杰,这是最醒目的评价。这个大器晚成的负重者角色由一连串的经历组成:8年造纸厂的学习和工作经历,28岁开始接触生物学,38岁还在做博后。在社会时钟深嵌所有人神经的当下,很多人会疑惑,“他会焦虑吗?”、“他是怎样做到的?”。我们把这些问题抛给他,他的回答带着些后知后觉的意味,“也许我当时应该焦虑,但我确实没有焦虑”。一路走下来,柴继杰的自我评价与外界评价是脱节的。当别人关心是否科班出身时,他满足于自己的获得感,“有机化学的课程学得不错”、“同学不错,我也很不错”、 “整个博后期间做得很顺,第二年就发了很好的论文”。他曾经说过“选择是一件极难的事”,但后来我发现他说的只是那个堆积与折叠的世界。他的人生选择是一条笔直又简单的通道,就像他的抗病小体一样,只需要关注上一步和下一步的事情。尽管中途多波折,选择有时也不由自主,但境遇逐步改善。他给现实世界分去了较少的关心和精力,活得也轻松自在,而他花大力气在分子尺度的辽远地图上驰骋。他很少会长时间感到沮丧,“只要我一直在思考,焦虑就追不上我”,坐在我们对面,柴继杰完全不像是一个已经57岁的中年人,言语间迸发的生命力恍惚觉得是一个40岁左右的青年人在挥斥方遒。他用他的经历表明:人只要一直在做事,跑起来,情绪的容器便不会漫溢。内心的充盈和丰富,连带着天然的钝感力支撑他走过许多外界认为的“困难”。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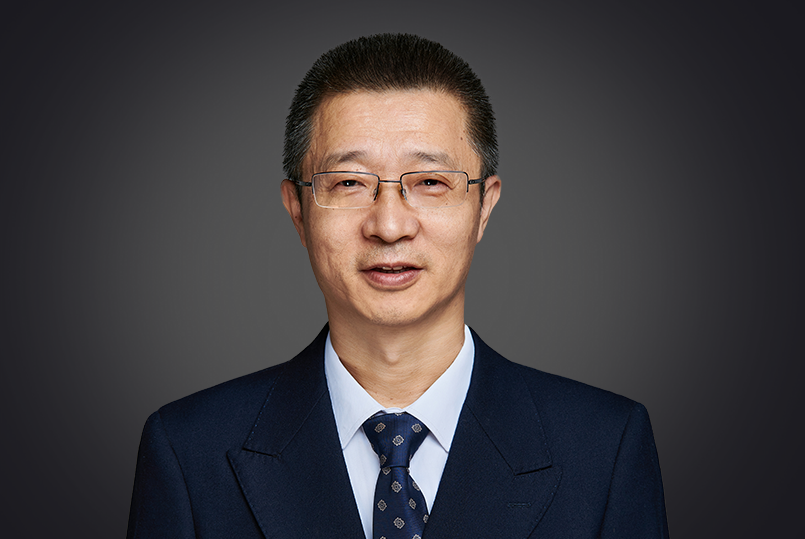
柴继杰,1966年生于辽宁,现为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免疫学讲席教授。1987年获大连轻工业学院纸浆造纸学士学位,毕业后进入丹东鸭绿江造纸厂担任助理工程师。1994年获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应用化学硕士学位,1997年获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药物研究所分析化学博士学位。1997-1999年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从事晶体学博士后研究,1999-2004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师从施一公院士从事结构生物学博士后研究,2004-2010年任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及高级研究员,2009-2023年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2017-2023年任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植物育种研究所“洪堡教授”。2023年8月,他与合作者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周俭民共同分享了本年度“未来科学大奖” 生命科学奖,获奖理由是“为发现抗病小体并阐明其结构和在抗植物病虫害中的功能做出的了开创性工作”。故事的两面
柴继杰的传奇故事,看起来是一个输在起跑线上的人如何绝地反击的励志叙事。
他真正跨入生物学大门的时候,已经33岁,比他的博士后导师施一公还要大一岁。
初次组建实验室时,施一公收到了六七十份简历,最后他将其中一个名额给到了这个来自辽宁的前鸭绿江造纸厂助理工程师,他说,“我就看重了他在工厂干了四年,能最后考回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做博士生的经历”。
普林斯顿大学报到的第一天,施一公介绍完研究课题和初步的实验设计,柴继杰依旧站在那里没有动。“一公,你能不能再讲一遍?”柴继杰问。“你听懂多少?”施一公反问。“我,可能大部分没太听懂……”。
2017年国家公派出国留学人员行前集训视频会议上,施一公分享道,“继杰在我那前两年就是技术员,他不明白他在做什么,因为基础太差了,手把手教他,第三年开了点窍,第四年有自己想法的时候我非常非常欣慰”。
柴继杰的履历也在加深这种印象。17岁上大学,学的是造纸,毕业后被分配到了丹东造纸厂,4年后去北京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跨行读了应用化学的硕士。28岁再次跨行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药物研究所读分析化学的博士。博后做了两段,从生物物理研究所晶体学转到普林斯顿大学的结构生物学,加起来花了七年。在每个阶段,他几乎都尝试了新的东西,以至于刚开始做博后时,连生物学本科生必备的PCR实验都不会。
社会时钟已成为现代人工作和生活的规范指导,任何企图挣脱的人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代价。有十多年,柴继杰一直游荡在时钟之外。起初我们猜测,柴继杰的坦然可能与时代的窗口期有关,重组年代社会节律的混乱、宽松包容的社会氛围,但后来我们发现没有任何关系,这是独属于柴继杰个人的特质,一种后知后觉的钝感力和内心的充盈与丰富。
柴继杰的自我评价构成了一段故事的另一种叙述,关于人的倔强、满足和骄傲。他从来没觉得自己输了或是不行。很少有人知道,他所在的普通高中,在1983年的夏天,他是唯一考上本科的学生。作为造纸大厂,丹东鸭绿江造纸厂的效益极好,新闻纸产量占全国的6%,分配的助理工程师岗位在那个年代很拉风。在工人们吵杂的牌局中,柴继杰边上班边复习了半年,非常轻松地考上了如日中天的石化行业的研究生。
愉悦的学习感受给予了柴继杰极大的归宿和满足感。柴继杰回忆道,“当时我们研究生班一共9个人,4个来自清华,其他也都是很好的学校,跟他们在一起我也觉得自己挺好的。我当时学东西比较扎实,无论在哪里考试,成绩都不错,博士生考试时有机化学考得格外好”。
按照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的规划,他应该考应用化学的博士,可他实在是太喜欢有机了,选择了考药物所的有机合成博士,但因为没有做合成实验的经历,又被转到分析化学的贺存恒导师手下做晶体学。“现在想起来所谓的喜欢,其实就是理论学得好一点,误以为喜欢,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柴继杰说道。
真正的科研训练刚刚开始,不过条件依然艰苦。导师贺存恒刚从国外回来,没有蛋白制备样品的条件,最后他们决定研究羧肽酶A与抑制剂的作用机制,先合成抑制剂,再解析其与羧肽酶A的复合物晶体结构,理解该抑制剂的作用机理。
尽管这篇论文现在看着毫不起眼,但柴继杰认为“从科研训练的角度来看,它仍然是一个不错的课题,拿到了我们需要的结果,发了一篇还算可以的文章。正是因为这篇文章,我在晶体学方面获得了一定训练,施老师才招我作为博士后”。
当他到了高手林立的普利斯顿,也没有让他感到沮丧或挫败。“很充实,每天都能学到不一样的东西,感觉挺嗨的。我去了不久,施老师和王晓东老师就有合作,发挥了我在晶体学方面的长处。第二年就发了一篇很好的文章,整个博后期间做得很顺”。负面的情绪总是产生在毫无头绪和止步不前中,而他每天都在奔跑。
故事的两个版本映照着自我和外界的两种投射,有关人如何在逆境中收获心灵的安定。
他的人生没有经过精确的操控,在一片迷茫中轻松愉快地度过,几乎每个专业选择都像是闭着眼睛摸索。那个信息缺乏的年代,他依靠一点运气、持续的努力,以及那些正向的回应,才顺利地跨入了科学研究的门槛。
十年
他获得未来科技大奖的工作,也是他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植物抗病小体,给了他研究道路上最大的挫折,最初的10年他们甚至连一个合适的抗病蛋白都没有筛选到。细胞表面模式识别受体介导的广谱性识别(PTI)和抗病基因介导的特异性识别(ETI)构成了植物免疫的两大防线。ETI中,具有核苷酸结合域和富含亮氨酸重复序列的NLR蛋白是其中的大家族。早在2004年北京昌平的秋天,他和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另一个年轻人周俭民一起选择了第二条防线,“抗病蛋白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彼时,动物和人体NLR的生化功能正逐步揭开,而植物则是一片荒芜,等待他们的是令人兴奋的巨大未知。彼时已经年满38岁的柴继杰放到现在,也许会被一众科研项目和人才计划的年龄线扼住咽喉,不过他是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首批研究员,作为科技体制改革的新兴试验田,在北生所不需要申请基金,每位PI每年就能有200—300万元科研资助。柴继杰的钝感力帮他跨过漫长的求学生涯,而他的幸运让他在PI生涯的最初跨过了千山万壑。谈到这种幸运他说,“我们不能决定时代,只能顺着往下走,那个时候我们各方面机会都很好。当时回来想的就是先干,没去想焦不焦虑,只是现在回想起来可能当时应该焦虑”。没人能想到他们之后的合作将跨越二十年,成为业内人人称羡的“黄金搭档”。周俭民致力于研究植物和微生物相互作用机理,当时他的实验室就在柴继杰对面,中间隔着一些共用的实验设备。拉近两人距离的除了物理空间,还有相同的“烟瘾”,一起吞云吐雾交流想法。愉快长久的合作在科研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金字塔体系中,成果意味着可以晋升的名利。“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是解决科学问题,在发表文章的问题上,我们没有去斤斤计较”,柴继杰坦言,“我一直感恩,若非来到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没有周老师,我不会走进植物免疫这个领域”。前排左一周俭民,左二柴继杰
图源:西湖大学
遗传学的“基因对基因”理论搭建了植物免疫的大厦,想要精准地改造植物,我们必须了解得更多。不同于人类身上专门的免疫器官和免疫细胞,每个植物细胞似乎都具备完整的一套免疫体系,抗病信号通过一系列的调节因子和基因形成复杂的调控网络。结构生物学企图理解每一个分子,它们如何揭开伪装、识别敌人、发动战争、打扫战场、总结战术。它们的折叠方式与空间构象对于分子的功能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掌握了分子的三维结构,就掌握了分子开启和关闭的钥匙。不过很多时候都是一块块小的拼图,破碎且零散,还原一条广谱、完整且精妙的防御之路是无数研究人员的梦想。第二道防线迟迟没有进展,除了2007年番茄抗性蛋白Pto“诱饵模型”激起的小水花,平静得像一潭死水。他们试了许多体系都不成功,直到2013年PANS发布了一篇关于ZAR1与其互作蛋白的研究,他们才把目光缩小到这个体系。与此同时,周俭民实验室关于ZAR1的研究也取得了重要进展,为他们之间抗病小体的合作奠定了基础。十年没有重要的研究成果怎么办?柴继杰笑着说,“我们靠模式识别受体研究支撑了许多年,绝大部分项目和经费不允许5年什么成果都不出,所以我们就多走几条路”。“做一些比较有挑战性的课题,很长时间不会有产出,钱从哪儿来?只能用其他研究来支撑”。他的另一条路是植物免疫的“前哨”,包括植物细胞表面受体激酶和受体蛋白。他们发现,植物免疫与植物生长发育中,二聚化是植物受体激酶活化的最小单位,而受体蛋白的活化也遵循“二聚化”的基本规律。这让他和他的团队获得了2017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同年他也受到了德国洪堡教席奖的认可,获得了500万欧元资助,前往德国开展为期6年的研究。轻重不一的脚印是他研究的印记,截至目前为止植物抗病领域现有的复合体结构几乎都出自他的实验室:2007年第一个细菌效应蛋白和植物中对应抗性蛋白的复合物(AvrPto-Pto),2013年第一个被解析的植物LRR模式识别受体复合物(FLS2LRR-flg22-BAK1LRR),2015年第一个植物肽类激素的激活复合物结构(PSK-PSKRLRR-SERKLRR)……可以说该实验室于全球植物抗病结构中领先。他非常知足地说,“有的人是「合适的时间遇到了合适的人」,有的则是「合适的时间解决了合适的问题」,这两个都让我遇到了”。
结构生物学家的幸运
2018年,当拿到中间凸起的紫金花抗病小体“照片”时,柴继杰发现自己曾经十几年理解的NLR作用模型可能被误导了。“它很有可能是一个channel,而不是adaptor”,柴继杰惊觉。1994年,第一个植物NLR抗病蛋白克隆完成,25年过去了, 人们对植物NLR的生化功能仍知之甚少。由于抗病蛋白构成复杂、分子量大且构象多变,高表达、纯化、重组困难,国际多个顶尖实验室都折在结构破译的路上。许多研究者自然而然联想到具有相似结构域的动物NLR蛋白,提出了adaptor的假说。柴继杰在普林斯顿研究人体的凋亡小体(apopotosome),在清华研究动物的炎症小体(inflammasomes),他也曾是这种假说的追随者:相似的寡聚物通常是一类接头蛋白,募集下游蛋白,调控抗病信号。在走错路的情况下,柴继杰一轮轮进行筛选,得到的是年复一年的失望。后来的数据表明,植物抗病蛋白确实可以作为阳离子通道。激活后的ZAR1蛋白在植物细胞膜上形成五聚体复合物,促进Ca2+离子内流,激活免疫反应和细胞死亡的机制。“以前从来没有人这么想过,但现在回看,以前的很多数据也都非常合理”,柴继杰恍然大悟道。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昕等人专文评述,“该研究是植物免疫研究的里程碑事件”。像一颗重磅炸弹,审稿人说道,“这项发现改变了学界对抗病蛋白触发细胞死亡的认识”。“我非常幸运,在我的一生中能遇到这样的东西,真真正正只有通过结构才能触及到它的本质,而不是其他手段”,作为一名结构生物学家,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分子。他是一个拒绝浪漫叙事的人。当我们问他“你觉得抗病小体美吗”,他笑着回答说,“我觉得挺美的,情人眼里出西施”。而一旦再继续追问,“你做了那么多结构,你觉得哪个最好看?”,那掺杂着薄薄滤镜的光晕瞬间破碎了,又马上严肃起来,“它不是好看,最重要是有意义”。柴继杰形容科学研究就像抽烟一样容易“上瘾”,普林斯顿是他上瘾的关键一步。上瘾,是不断得到积极回应的情况下产生的。柴继杰的解释融入了无数人的日常,那些仅有自己解答出的题目、一门拿高分的课程,以及发表文章后获得的认可。迷恋学术研究,宛如一种瘾,或者说是一种快感和喜好,甚至成为柴继杰人生的价值所在。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在研究上投入了大量时间,频繁熬夜,周末也难得休息。那时候施一公时间也充沛,实验室老师学生加起来也才三个人,柴继杰的生物学实验技术是施一公手把手亲授的,绝对的嫡传,就这么扫盲了半年,情况才逐渐好转。即便到现在,他也一周保持着至少80小时的工作时间,经常是第一个到实验室,最后一个走。柴继杰的脑子里总有一块地儿装着他的研究,快走锻炼、吃饭睡觉,无时无刻不想它。他坚信真正的热爱和专注是不分时间地点的,他常用一个生动的比喻与学生们分享,“就像你对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肯定不是只有见面时才想起他们,至少在没有见到他们的时候,你也会不自觉地思念,这才是爱的最低标准”。他专注的这个领域给了他最多的情感的回馈。他说,“我有一个朴素的想法,国家出钱让我维持自己的兴趣,我砸也要砸出个响来,才能不辜负国家对我的信任”。或许因为过于专注,他很少会长时间感到沮丧,“只要我一直在思考,焦虑就追不上我”,坐在我们对面,柴继杰完全不像是一个已经57岁的中年人,言语间迸发的生命力恍惚觉得是一个40岁左右的青年人在挥斥方遒。而另一件让他上瘾的东西——香烟,则一次次败下阵来。最开始是因为普林斯顿附近没有国内数量庞多的小卖部,需要到非常远的地方才能买到一盒烟,为了节约时间,他索性戒烟了,那之前他几乎一天就要抽上一包多的烟。到了2005年,回国后的第二年,他又复吸了。由于胃病的缘故,他在德国马普所彻底告别了香烟。他给自己制定了一套“比较tough的方案”:将烟放在办公桌上,放在自己面前,不断让自己脱敏,等到回家看不到香烟,就轻松多了。“说到底,抽烟人总是能为自己找一大堆理由,吃完饭后干什么,下飞机后做什么,第一个浮现在脑子里的总是抽烟这个念头”。许多人切断依赖性事物恨不得离得越远越好,这会减轻自我控制的痛苦,而柴继杰选择了一种精神胜利法,他总相信自我意志的价值,花了三个月戒了他抽了几十年的香烟。选择
他曾经说过“选择是一件极难的事”,但后来我发现他说的只是那个堆积与折叠的分子世界。他的人生选择是一条笔直又简单的通道,就像他的抗病小体一样,只需要关注上一步和下一步的事情。尽管中途多波折,选择总是不由自主的,但境遇逐步改善。他给现实世界分去了较少的关心和精力,活得也轻松自在,而他花大力气在分子尺度的辽远地图上驰骋。

他说,“选择一个正确的方向然后慢慢专注,意味着成功了一半甚至更多”,科学研究是一个拨云见雾的过程,从错误的信息中逐步筛选出正确的东西,获得一些线索或启发,再找一个从时间和金钱成本上都比较合适的路线。选择一个科学问题很难,选择一个正确的方向就更难了。每个领域都有密集爆发的时期,两三年之内就能接受百年变迁的洗礼,也有踟蹰不前的时期,没人知道现在自己处于波峰和波谷之间的什么位置,科学的发展没法预测。柴继杰放弃了炙手可热的动物细胞凋亡,和他的搭档一起专注植物免疫,转换方向是因为未知,被未知的抗病蛋白吸引。柴继杰反对那种实验卡在某个地方,继续反复的行为。他举例说,在普林斯顿一个关于表达蛋白的课题里,实验通常在22°C到24°C进行,有一天他突发奇想,想试试温度放到16°C会怎么样?一个微小的变化最后产生了巨大的差别。他的师妹、深圳湾实验室主任颜宁常常评价他“不按常理出牌,许多课题不拘一格突破瓶颈”。他回应说,也许我当时没有在“圈”里,缺乏传统知识背景,这反而让我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思考问题。动物的NLR蛋白NLRC4的自抑制研究也是让柴继杰感到非常艰苦的课题,“那真是每一步都是坎”。这条路谈不上非常险,也说不上方向不对,只是没有走在合适技术周期上。那是2013年,冷冻电镜技术爆发的前夜,清华的高分辨率冷冻电镜两年之后才落成,而他们的研究成果2013年已经发出来了。那段经历简直是一路坏消息不断,“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晶体结出来,结果晶体X射线衍射的能力非常弱。获得衍射晶体之后,结果数据收集又出问题了。正常情况下,收集几分钟,晶体并无异常,但是NLRC4的晶体,在上海的同步辐射光源照了几秒钟之后,晶体马上就衰减了。之后又去改变条件提高晶体在X光下的稳定性,这又花了很长时间”,而后的结构解析又经历了很多的曲折。“老实说,我当时都觉得很沮丧”,这是采访中柴继杰唯一承认的沮丧。但是让他欣慰的是做这个课题的研究生胡泽汉一直坚持不懈。这个课题使他更进一步认识到,科研中坚持的重要性。有时候柴继杰也会假设,假设重新回到38岁成立实验室的节点,他想要把曾经选错的弯路都纠正。说这话时,他无不遗憾与惋惜。分子世界有千千万万条路,如何选一条对的路?即便是现在,对于柴继杰而言,依旧是一个天问。他还在不断拨云见雾。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3LERO8NICFtxnaXiH1NHrQ